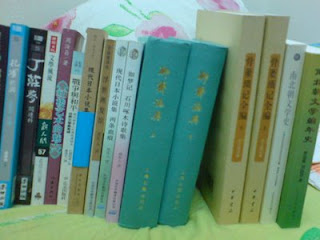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從一個美國漢學家處知道,原來西方學者和東方學者,彼此之間一直存有偏見。西方漢學家批評中國學者的學術動機常常是發揚中國文化的偉大和獨特,而非一種客觀學問。而中國學者則認為大部分西方漢學家不如自己對中國文獻資料掌握得更熟悉,因此認為西方漢學家大都衹會大談理論,并試圖以自己的理論為基礎,再對某一問題尋找答案,形成一種牽強附會。雖然這種認知在很早以前就已在漢學界成為普遍共識,在中港臺也可能已經不是甚么新鮮事,然而余生也晚,直到今天,才知道這一偏見的存在。當然,這裡不是要討論雙方之間的偏見問題,還輪不到我來發表,而且可能隨便上網一搜就能搜到相關論爭了。想說的是,在一般人眼裡學富五車的學者,卻原來也存在著這種問題——偏見。
偏見之產生原因,沒其他,衹因為不了解。
這幾天又發生了些令人喘不來的事件,癥結便在於偏見。還好有一件因為自己的及時發現,來得及懸崖勒馬,雖然在心裡也長了難滅的疙瘩。至於另一件,好像是無疾而終了,雖然我由始至終都認為自己并沒大誤,衹是,當時沒顧慮太多,導致距離被拉開了。然而意外的是,在一個靜寂的夜晚,卻來了信。上上下下重復看了三遍,終於也回信。過多幾小時,也收到回信。一樣,上上下下重復看了三遍。這時,我不知該怎么回了……再多讀兩遍,也依然不曉得該如何回。也罷了,人生原就是由很多個遺憾組成的……所能做的,盡量避免這一切遺憾的再次發生而已。紀念,是為了忘卻?忘卻,是為了紀念?我不知道我是為了忘卻還是為了紀念。罷了罷了。
看章太炎的〈四惑論〉,越看越惑。當中提及,「蓋人者委蛻遺形,倏然裸胸而出。要為生氣所流,機械所致。非為世界而生,非為社會而生,非為國家而生,非互為他人而生。故人之對於世界社會國家與其對於他人,本無責任。責任者後起之事。必有所負於彼者,而後有所償於彼者。若其可以無負,即不必有償矣。然則人倫相處,以無害為其限界。過此以往,則鉅人長德所為,不得責人以必應為此」。意思大概是,人與人之間在社會建立的關係,選擇權大都在自己身上。一切社會制度亦是為了每個個體的自持自守而建立。天道無親,人道無常,所以個人對於集體原本就不存在著任何內在義務。倘若以所謂社會道德或責任強令一個人為社會服務或犧牲,這是本末倒置的。因此,章氏認為個人對社會不負回報之責任。
從一個美國漢學家處知道,原來西方學者和東方學者,彼此之間一直存有偏見。西方漢學家批評中國學者的學術動機常常是發揚中國文化的偉大和獨特,而非一種客觀學問。而中國學者則認為大部分西方漢學家不如自己對中國文獻資料掌握得更熟悉,因此認為西方漢學家大都衹會大談理論,并試圖以自己的理論為基礎,再對某一問題尋找答案,形成一種牽強附會。雖然這種認知在很早以前就已在漢學界成為普遍共識,在中港臺也可能已經不是甚么新鮮事,然而余生也晚,直到今天,才知道這一偏見的存在。當然,這裡不是要討論雙方之間的偏見問題,還輪不到我來發表,而且可能隨便上網一搜就能搜到相關論爭了。想說的是,在一般人眼裡學富五車的學者,卻原來也存在著這種問題——偏見。
偏見之產生原因,沒其他,衹因為不了解。
這幾天又發生了些令人喘不來的事件,癥結便在於偏見。還好有一件因為自己的及時發現,來得及懸崖勒馬,雖然在心裡也長了難滅的疙瘩。至於另一件,好像是無疾而終了,雖然我由始至終都認為自己并沒大誤,衹是,當時沒顧慮太多,導致距離被拉開了。然而意外的是,在一個靜寂的夜晚,卻來了信。上上下下重復看了三遍,終於也回信。過多幾小時,也收到回信。一樣,上上下下重復看了三遍。這時,我不知該怎么回了……再多讀兩遍,也依然不曉得該如何回。也罷了,人生原就是由很多個遺憾組成的……所能做的,盡量避免這一切遺憾的再次發生而已。紀念,是為了忘卻?忘卻,是為了紀念?我不知道我是為了忘卻還是為了紀念。罷了罷了。
看章太炎的〈四惑論〉,越看越惑。當中提及,「蓋人者委蛻遺形,倏然裸胸而出。要為生氣所流,機械所致。非為世界而生,非為社會而生,非為國家而生,非互為他人而生。故人之對於世界社會國家與其對於他人,本無責任。責任者後起之事。必有所負於彼者,而後有所償於彼者。若其可以無負,即不必有償矣。然則人倫相處,以無害為其限界。過此以往,則鉅人長德所為,不得責人以必應為此」。意思大概是,人與人之間在社會建立的關係,選擇權大都在自己身上。一切社會制度亦是為了每個個體的自持自守而建立。天道無親,人道無常,所以個人對於集體原本就不存在著任何內在義務。倘若以所謂社會道德或責任強令一個人為社會服務或犧牲,這是本末倒置的。因此,章氏認為個人對社會不負回報之責任。
 但我想問的是,這不是衹有隱士才能過到的生活么?的確,如果遺世獨立,則社會大眾便沒辦法過問。前提是「如果」。由於人類是群居而居的生物,彼此之間必然少不了來往,也因此就免不了應酬和互助的活動。而且勾心斗角,為了自身利益而加害於人,實在屢聽不鮮。這樣子生活,好累人的說,難怪魯迅那么不愛應酬赴宴,衹關在書房裡頭,寫寫文章,輯校古籍,也聞窗外事,爽爽就去看電影,不然知己學生來訪,但就是不跟外界有實際上的交道。落個耳根清凈!
先前讀了一篇外國漢學家的論文——〈孔子:野生的聖人,感運而生的神話典型〉。哇嗚!讀得我眉飛色舞(沒辦法,就像一個剛剛入城的孤陋寡聞的鄉下人,看到甚么都很覺新穎,衹是對於城裡人來說,早就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裡頭把中國自古以來最有名氣的歷史人物孔老爺爺,考證成一個「非人」:「孔子的歷史真實性是大可爭議的,孔子很可能像周人高祖后稷一樣,最先也是源于神話傳說,到了戰國時代才演化成歷史人物。」
歷來對孔子出生的說法都是根據司馬遷《史記》裡頭的〈孔子世家〉,說到孔子的母親癥在女士(還沒過二十)是通過郊外(野)的祭壇祭祀,向生殖神祈禱請愿,然後就和孔子老豆叔梁紇(蠻老的一個老頭子,超過七十歲了)就地交合,生下了至聖先師。所以李零在他那本《喪家狗——我讀論語》裡頭便說孔子是野種(應該是就事論事,無褒貶義)。於此作者引了日本學者白川靜的考證,說到按照那時候的婚姻習俗,像孔子父母的婚姻應當是恰當的(他用了「應當」兩個字)。所以,就算是「野種」,也是合法的野種。而後,作者引《孔子家語》中對孔子的出生傳說,來佐證他的見解,說孔子母親獨自一人在尼邱旁祈禱懷孕,求求一下,累了,於是睡覺。在夢中,看到黑帝,被搭訕後,「已往,夢交」。於是,她真的懷孕了。而那個叔梁紇原來衹是個幌子。
不過說也奇怪,通部《論語》,好像并沒看到孔子談論他父母的只言片語,對一個那么重孝道的「非人」來說,有點反常。當然,我們知道《孔子家語》是本偽書,但裡頭所收錄的,據說都是民間以口傳口的聞見,至於有沒有淪為以訛傳訛,則不得而知。
結果,讀了後生出了個問題:到底歷史上有沒有孔子這個人。
於是,我聯想到耶穌。原來,歷史上幾乎所有的聖賢人——如三皇五帝、大禹、后稷、孔子等——和耶穌一樣,都無生父的。過程是,神的來訪——奇異的受孕——輝煌地誕生——奔波的一生,最後變成偉人,然後名流千古。又有個問題,是不是說每個聖人的母親,都必須是冰清玉潔之身,才可以生下他們?不然就對聖人「不凈」/「不敬」?
還真是不謀而合。
意興闌珊。好不爽。
但我想問的是,這不是衹有隱士才能過到的生活么?的確,如果遺世獨立,則社會大眾便沒辦法過問。前提是「如果」。由於人類是群居而居的生物,彼此之間必然少不了來往,也因此就免不了應酬和互助的活動。而且勾心斗角,為了自身利益而加害於人,實在屢聽不鮮。這樣子生活,好累人的說,難怪魯迅那么不愛應酬赴宴,衹關在書房裡頭,寫寫文章,輯校古籍,也聞窗外事,爽爽就去看電影,不然知己學生來訪,但就是不跟外界有實際上的交道。落個耳根清凈!
先前讀了一篇外國漢學家的論文——〈孔子:野生的聖人,感運而生的神話典型〉。哇嗚!讀得我眉飛色舞(沒辦法,就像一個剛剛入城的孤陋寡聞的鄉下人,看到甚么都很覺新穎,衹是對於城裡人來說,早就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裡頭把中國自古以來最有名氣的歷史人物孔老爺爺,考證成一個「非人」:「孔子的歷史真實性是大可爭議的,孔子很可能像周人高祖后稷一樣,最先也是源于神話傳說,到了戰國時代才演化成歷史人物。」
歷來對孔子出生的說法都是根據司馬遷《史記》裡頭的〈孔子世家〉,說到孔子的母親癥在女士(還沒過二十)是通過郊外(野)的祭壇祭祀,向生殖神祈禱請愿,然後就和孔子老豆叔梁紇(蠻老的一個老頭子,超過七十歲了)就地交合,生下了至聖先師。所以李零在他那本《喪家狗——我讀論語》裡頭便說孔子是野種(應該是就事論事,無褒貶義)。於此作者引了日本學者白川靜的考證,說到按照那時候的婚姻習俗,像孔子父母的婚姻應當是恰當的(他用了「應當」兩個字)。所以,就算是「野種」,也是合法的野種。而後,作者引《孔子家語》中對孔子的出生傳說,來佐證他的見解,說孔子母親獨自一人在尼邱旁祈禱懷孕,求求一下,累了,於是睡覺。在夢中,看到黑帝,被搭訕後,「已往,夢交」。於是,她真的懷孕了。而那個叔梁紇原來衹是個幌子。
不過說也奇怪,通部《論語》,好像并沒看到孔子談論他父母的只言片語,對一個那么重孝道的「非人」來說,有點反常。當然,我們知道《孔子家語》是本偽書,但裡頭所收錄的,據說都是民間以口傳口的聞見,至於有沒有淪為以訛傳訛,則不得而知。
結果,讀了後生出了個問題:到底歷史上有沒有孔子這個人。
於是,我聯想到耶穌。原來,歷史上幾乎所有的聖賢人——如三皇五帝、大禹、后稷、孔子等——和耶穌一樣,都無生父的。過程是,神的來訪——奇異的受孕——輝煌地誕生——奔波的一生,最後變成偉人,然後名流千古。又有個問題,是不是說每個聖人的母親,都必須是冰清玉潔之身,才可以生下他們?不然就對聖人「不凈」/「不敬」?
還真是不謀而合。
意興闌珊。好不爽。
等待破曉的曙光,希冀看到旭日從東方破浪,照滅殘留在心底已大量失去的原本以為不了的情緣——徹底的。
不才峰啟:為報所謂師恩,奉命近日交還百令吉,恕難從命!吾班一百又十一人,今去其一,為一百又十人準。竊嘗計,每人一百,合計一萬一千。一萬一千,可謂天文數字。蓋不才乃窮書生,一輩子沒見過如此巨款。一萬一千,以報師恩,可謂盛矣。然,一萬一千,似亦已可舉辦學術研討會,是邪非邪?夫班中藏龍臥虎,不少少爺小姐,或系出名門,或富賈之後,皆千金之身,萬乘之尊。一百令吉,對此等上流人而言,不過小錢,倘用來塞牙縫,仍嫌綽綽有餘。奈何不才出身小康,錢財有限,胡亂揮霍,難向家中兩老辭咎。兩老食稀飯,不才食高品,可乎?如此做法,徒添不肖罪名,天亦必譴余。加之不才衣柜貧窶,無華服,缺艷裳, 西裝領帶,不過奢想。觀余平日所著之服飾,皆陋丑無華,以此丑陋裝飾出席高貴盛宴,不亦辱沒汝等之精心設計乎?汝等以「老師是我們的,就算不要去,也一定要還」為口號,逼迫不愿去之同窗,以乖乖就范。不才深以為不齒!竊以為,汝等所盡心盡力辦之謝師宴,不過借師之名,以求自娛。奈何,不才娛不起,實難就范。又,自踏入所謂「不歸路」起,不才深深迷戀書籍。因此之故,倘有閑財,皆報之以書。汝等愿去,則去;錢,愿還,則還。於此不才謹以拳拳之心,悛悛之貌,祝爾等盡興而歸。今,不才所思量者,乃腳踏大地,仰望星空,巨人肩膀,俯視同流。或曰:「幸於始者殆於終,繕其辭者嗜其利。」慎之慎之。故,所謂仰望星空云云,不過妄言佞語,亦是癡人說夢。然,除此之外,不才暫無他想,甚么服裝表演大會,甚么百令吉,皆拋諸腦後,九霄雲外。Last but not least,若能如故往,無怨無隙,妙哉!然,倘不齒余之一切言論,欲與割席,則請自便。謹此。
「黯然魂銷者,唯別而已矣。」 小時候讀《神雕俠侶》,讀到這句時,很覺心動。而後,才知道,原來是出自距今約一千五百年前一個名叫江淹的人之手,否則在那之前都還一直懵懂的以為是出自金老先生的手筆。江淹是誰?便是「江郎才盡」裡的江郎是也。江郎才盡的故事無人不曉,如果真的不曉,百度一下,谷歌一射,你就知道。 江郎的代表作,有人說是〈恨賦〉和〈別賦〉。也確然無可厚非,除了因為它們被南朝蕭梁眧明太子收錄在《文選》(拉大的「文選」也有收錄這兩篇名篇)裡頭并成為唐宋士子必讀佳品之外(那個喝醉酒撈月而死的李少俠,好像就是因為受到他的影響,寫下了另一篇〈恨賦〉),其實還是因為悲劇和喜劇,歷來都是前者吃香,畢竟,人類唯一生命的共感,便是悲劇了。就好像林黛玉動不動見到幾片落葉就哭,俘虜了多少癡男怨女的孤心,雖然這樣的女子娶回家的話男方一定沒日安寧。而這兩篇賦,你要有多悲涼就有多悲涼,要有多凄婉就有多凄婉,歷史上各類悲劇人物悲壯的一生,一一躍然紙上,他「寫出了或飲恨吞聲,或依依惜別時的各種感人至深的場面,把這兩種最能激動人心的感傷情緒摹寫得非常形象化」。從中你就可以知道江淹這個人有多怨有多愁了。 銷魂這兩個字,很奇怪,因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你高興,叫銷魂;你傷心,也叫銷魂。不過如果把它和酒一起來看的話,就見怪不怪了。因為,你高興時,喝酒慶祝;你傷心時,也借酒消愁。因此女人總愛問,你們男人為甚么這么奇怪,不管高興還是不高興,都喝酒。這都得歸咎於孔子的孫所提倡的「中庸」,而喝酒,就是「中庸」的表現了。 在古代,交通沒那么發達,所以一次別離,幾成永訣。也難怪古人對別離特別看重,投江屈死的屈老爺,便說過這么一句話,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不怪乎江兄對別離感到那么郁悶了。放在交通那么發達的今天來看,這篇名賦,還能震撼多少人心呢?不曉得。衹是,目前,據我所知,有個同窗,因病停學,和她相好的朋友,便都沉在一片愁云裡,有個人甚至還給她念了首挽歌。
「是以別方已定,別理一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此番別離,何時再聚,天曉得。親愛的朋友,惟愿,一切珍重。 離離合合平常事,風風雨雨一代人。 祗能說,人啊人,有時候,已經身在絕望之中,卻還得承受更大的絕望。時移世易的感傷,我們囬不去。破壞中再受破壞,陷入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虛妄,原來衹是另一種迷惘的詮釋——衹是當時已惘然。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柯條未曾損,盤根不曾移。同類今齊茂,孤芳忽獨萎。仍憐委地日,正是帶花時。碎碧初凋葉,落紅尚戀枝。乾坤無厚薄,草木自榮衰。欲問因何事,春風亦不知。——唐·白居易〈薔薇花一叢獨死不知其故因有是篇〉
柯條未曾損,盤根不曾移。同類今齊茂,孤芳忽獨萎。仍憐委地日,正是帶花時。碎碧初凋葉,落紅尚戀枝。乾坤無厚薄,草木自榮衰。欲問因何事,春風亦不知。——唐·白居易〈薔薇花一叢獨死不知其故因有是篇〉
昨天,目睹了一個生命的流逝。「嗙!」一聲巨響後,所有人——第一樓至第十二樓——均第一時間往遮欄處靠,幾百幾千雙眼紛紛搜尋那聲巨響的來源。是女生,二十來歲模樣(然而據今天新聞報導說是三十五歲),臉蛋端秀,血不停從她下半身漫延,是失足而墜呢還是蓄意而墜,我不知。頃刻,五來個好心人士給她做人工呼吸,一個累了換另一個,如此循環往復,過了三十分鐘,依然沒蘇醒。直到一襲黑布將她給包裹後,我才離去。我想,這場意外,應該足夠多事的人們(如我)「回味」上幾天。衹是說,「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鑒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滓,衹值得煩厭和唾棄」。過了幾天,事情淡了,回味的價值也貶了,她也就真正地死去了——誰也不會放在心上。
後來聽聞那位小姐原來有憂郁癥。說說她的死。如果真是她自己所選的,我感到欽羨(好干脆俐落,如此就避開了人世間的所有苦)。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死法,今難再見,因此之故,我猜想她應該是因為難忍之苦所以選擇了死(都說了人家有憂郁癥,不是因為難忍之苦還能因為甚么?)。難忍之苦有如失戀、破產、患絕癥等等,不是說因為她不怕死所以才選擇了死,人多是貪生怕死,衹是因為生時已有苦,所以才避苦捨生尋死。那些假道學的人們,我強烈要求你們別又自以為是的發表一番謬論來輕蔑她,畢竟每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一旦超過了那極限時,便是要求解脫了,而死,往往是他們能想到的最好解脫方法。對死者而言,死了,一切悲劇就覆滅了。衹是說,若沒有那難忍之苦,誰會捨得去死,她也會和常人一般平凡開心地活下去的。
說到死,這是我從小把玩牛角尖時最愛鉆的課題了。然而鉆了那么久,至今,我仍不確知,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未知生,焉知死」,是對的。再說生死問題大都是有了一定年齡的人才會去碰的,以我如此稚嫩的年齡而言,在此小談生死,大放厥詞,實在是於理不合。但俗人(如我)往往就是如此犯賤,對於越是不知道的事物, 就越是有興趣知道。
家裡信奉佛教, 遵循的是南傳教義。家母每朝起床後做的第三件事便是在地上鋪草席,草席上擺設小案,案上擺一本經書與盛水的佛器,手中拿著由一〇八顆珠子串成的念珠。準備就緒,張開口,鼓動舌,總是以南無塔剎起句,於是乎開始了一日之計。(第一件事是沖涼,第二件事是給先人上香)。我便是在如此背景中長大的。因此,對於死亡的概念,一言以蔽之,曰:「輪囬轉世,善惡有報」是也。即是說,一個人,死後仍會生,生後還會死,死的衹是軀殼,靈魂則永恒不滅——生命是輪囬的,死了仍能重來(忽而想起「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鳥話來)。
然而,越長越大,對於這種生死循環的概念,卻逐漸變了質,皆因不知在幾歲的時候起,有個疑問生發在我腦裡,這疑問讓我從相信輪囬到質疑輪囬,即,如果靈魂不滅,生生不息,那么,地球上的人口的滋長該如何解釋?這些多出的靈魂究竟從哪里來?自那時起,對我而言,死,不過是滅的同義字,滅後,則永恒消失,不復轉生。說到這裡,怕且有人要問,「那么生命有什么意義」。這是人生哲學上永恒的爭論,我不是哲學家,自然掠過不談,衹是說,對我而言,生命是無意義的,所以當我看到那位小姐靜靜的躺在地上時,心中雖蕩起了一陣波瀾,但頃刻即止,就好像去戲院看悲劇時, 還錢買眼淚,戲落幕了,眼淚也就止了,或者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觀看悲慘事件能夠使一個人的情感得以抒發」,即此之謂歟。若躺在那裡的換作是我熟識的人呢?我會如何?我想,我會流淚——這是正常的反應,超脫如阮籍者在聽到母親的死訊時沉默了五分鐘後不也是心慟難當咯血昏厥?雖然有不少人說他衹是表面上超脫。不是說看輕生命就不會因生命的流逝而不感傷痛,畢竟落紅也是有情的。然而哭過悲過,我還是我。
生孕育死,而死又不過是走向生。
《牡丹亭》中那位懷春少女杜麗娘,看到園子裡「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坦,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時,不禁想起夢中情人對她說的「衹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似水流年……一陣風後,杏墜春消,結果?甚么也沒留下,似水流年,來去無痕,我們衹不過是在那不仁的天地中被當作芻狗來玩的其中一物,倘看到芻狗們不受控制了,祂就爽爽來一場大洪水,湮滅萬物,從新來過。不過上帝我想對袮說,如果下次再要放水的話,請別通知誰誰造甚么方舟了,就干脆點,甚么都別留下,一了百了,永絕後患。善哉善哉。
「今來古往無不死,獨有天地長悠悠。」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悲夫!
 夜中不能寐 起床至公園身顫侵寒煙 前愆百慮煎葉上一蝸牛 瑟縮螺殼間匍匐有牽掛 沉湎歲月淹
夜中不能寐 起床至公園身顫侵寒煙 前愆百慮煎葉上一蝸牛 瑟縮螺殼間匍匐有牽掛 沉湎歲月淹
夜間獨徘徊 風起舞塵喧風停塵囂止 茫茫奈何天
往者難再諫 情誼不再鮮獨坐秋千上 孤懸天地間
月兒幾回變 人事幾回遷
長夜空寂寞 無語問蒼天
後記:
許是下午喝茶太過,咖啡因作祟,導致如今怎么翻怎么覆也不能睡。想起友人說今夜的月亮是十五年來最大的,於是孤身走去公園……
月色確然明媚,有稀星點綴。難得沒人,就順便蕩了一會兒秋千。不經意看到一隻蝸牛,靜靜不動的,不知是沉睡著還是沉思著……
終于還是囬了房,依然難入睡。心血來潮,翻回那年的書函,一張張一字字沉緬一番……
字跡如舊,我於是惦念著,尋味著,這種遮蔽的欣慰,卻因為人臉的全非,心裏也很起了一陣莫名的傷悲。
也罷。恰如孫綽所言的:
「樂與時過,悲亦係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跡,明復陳矣。」
「『不讀書而好求甚解』,幾成中文系學生的通病。尤其是「才氣橫溢」的北大學生,更是喜歡高屋建瓴,指點江山,而不習慣含英咀華,以小見大。重理論闡發而輕個人體會,重歷史描述而輕文本分析,我擔心,長此以往,文學教育這一最具靈氣與悟性的課堂,將變得嚴肅、空疏且枯燥乏味。有感於此,本課程轉而強調讀書時的個人體味、研究中的問題意識、寫作中的述學文體等。」(陳平原《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
以上這段話乃陳氏於北大所開的明清散文研究課程(類咱校的「元明清文選」,自然,此所指者不過課程名字之相像而已)對他口中才氣橫溢高屋建瓴指點江山的北大生的開場白。
關於「不讀書而好求甚解」這句話,追根溯源,當是化自孔子對子游的「蕩人」之誨,即「好知不好學,其弊也蕩」是也。對於「幾成通病」云云,我看後之所以會心 一笑,并對冀兄說「罵得好」,乃有見於如今自己與周遭同學的學習態度,皆因自己實在懶散,卻又對各方知識有濃烈興趣,自然而然的就對號入座了。之所以那么憧憬五四,就因為那時代的讀書人大都學貫中西,通今博古,甚至音樂畫像均有涉獵,是通人而非殘障人。
陳平原這句話是對北大生說,所以自有其一定道理在。如果他來到拉大中文系對我們重復一遍的話,則實在是沒道理可言了。皆因我們求學態度乃「輕理論闡發」 而「重個人體會」,甚么甚么文選也好,甚么甚么專題也罷,都是很「重個人體會」的。當然,我不是說重個人體會不好,正如某先生所言,「我教哲學呢, 最終目的是希望你們能將它們應用在生活上,好讓這些哲學知識在你們遇到困境時能夠給你們有不同的思考空間,這樣子就能夠從容地面對難題了,知道嗎?」 教書先生的良苦用心,我還是體會得的,祗是說,物極必反月盈則虧,太多的「個人體會」,如此不著邊際天馬行空,會漫無所守而終致「蕩人」的。對了,那位先生語重心長說完那段金玉良言后,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天,又要灌雞湯了」。俺虛不受補啊。再說,你先天殘障就先天殘障了,再怎么補也醫不好的了,不會因為懂了幾堆道理後就煥然一新,從此變成仁人孝子的。
可以說,我校課程大多是偏重於個人體會的,所謂「好求甚解」是也,亦即是「多思」。這也無可厚非,因為我們眼前的實際生活依然是思想的源頭活水,「學而不思則罔」嘛。那些訓詁、目錄、版本等等,學來何用?死板板的一套東東,對思想并沒助益,更不會幫你成為一個大作家,反而七把劍五把刀藤井花等,這才是生活的圭臬,思想的主流,皆因其說處處貼近自身,能夠激活天馬行空的思維方式的。當然,先生們也是知曉「思而不學則殆」的,衹是說對於咱這群「才情橫溢」又「好為人師」的中文系生而言,走的路子是魏晉玄學派的,雖然祗得其末流,但怎說也高人一等,見山不是山了。噢,聽說下學期的甚么甚么創作,又好像是非常著重個人體會的課程了。 趁還有一個月時間,我要趕緊天天打坐,學學釋迦,日日苦思冥想,超脫人世的羈絆,以便達到見山不是山再晉升到見山還是山的最高境界。呃……上完了能否成為大作家我不懂,但是,多多少少應該是有資格當個小小導演,出來社會時有一技傍身的了。
后記一:昨夜,我夢到我去了北大,旁聽了陳平原先生的課時,他說:「『好讀書而不求甚解』,幾成中文系生的通病。尤其是「好高騖遠」的XX學生,更是喜歡得意忘言,見山不是山,而不習慣含英咀華,踏踏實實讀書。重個人體會而輕理論闡發,重文本分析而輕歷史描述,我擔心,長此以往,中文系這一最具靈氣與悟性的課堂,將變得輕佻、浮華且不著邊際。有感于此,尼采的『上帝已死』或羅蘭巴特的『作品一出作者即死』的說法,將從此在此課程中完全摒棄,從而回到『知人論世』的傳統學習方式。」夢裡所聽得的,醒來後還是總覺不對勁。後來想一想,將「好」改成「不」,即「不讀書而又不求甚解」,方是我那無可救藥的病癥吧。
后記二:雜亂無章,亂說一番,不知自己正表達什么。無法度,我受雞湯餘毒頗深,難免就偏重於個人體會了。
后記三:此文原是想回應冀兄的〈不讀書而好求甚解〉,但寫了幾行後,卻變成騷體文了。「吐盡泥水也吐不盡牢騷」,還是就此打住好了。